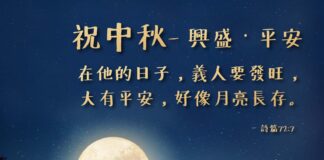凌是我大学同学。记忆中,这位与我上下铺的同窗一直是时髦雕琢的。八十年代初,女孩子最流行的发式是马尾巴。凌的马尾巴还有些自然卷曲,加上她身材高窕,笔挺的喇叭裤,还有颜色搭配得很好的碎花短袖衫,很引人注目。刚进学校那年,我们宿舍的女生总是在午睡后准时起来,梳洗好了,全都坐在宿舍看书。凌也在这时候打扮整齐,跟朱同学出去,说是去外面什么地方游泳去了。
朱更是时髦青年,入校时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,办好了美国签证,随时准备出国。系里第一次办晚会,凌和另一位漂亮女生,还有高年级的两位帅哥,表演四人舞,很酷。
黄昏的时候跟凌一道去图书馆晚自习。走出我们住的广寒宫,沿着东湖边那条小径,左边的树林飘过来一阵炊烟。她掏出白手绢,刻意地咳了两声。大城市里来的闺秀,闻不得那味儿,烟熏火缭的,呛人。我暗暗的把脸侧过去,对着那烟香畅畅地吸了两口,心里一阵惊喜:久违了!
如烟往事飞逝,廿年瞬间就过去了,才再次有了彼此的消息。我只知道她大学一毕业就去美国读硕士,很快就信主了;她的先生做教授,还是一间教会的长老。这不奇怪,教会总是选德高望重的弟兄做长老,她先生刚四十出头就已经是终身教授,不简单。
奇怪的是,有一次牧师讲道说,他刚从美国一间教会带培灵会回来,并说那个教会的长老,也就是传道人,辞去终身教授职位,去做宣教士,实在了不起。我第一反应是,该不会是在说凌一家人吧?我在凌那里得到证实,令我敬佩,于是参加了他们宣教的祷告伙伴网,每月会收到他们的信,告知近况和代祷事项。一路看他们走过来,令我深深感动。大人不容易,孩子们就更难了。两个十几岁的孩子,离开了他们熟悉和喜爱的美国,离开他们美丽的家,离开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,离开他们咫尺可达的哈佛耶鲁优越校区。这一切,只因为是神的呼召,只因为父母从来都是把神的事放在第一位。
几年过去了,就在我成了不冷不热,自己都感到厌倦的一种基督徒形态时,偶然翻到几本旧杂志,打开一本《生命季刊》,第一眼就看到了凌和先生的名字。那里登了他们长长的见证,这时我才真正了解我的同窗:她不再雕琢。与同是学者的先生一道,他们在教会做的是最为“瓦器”的工作,每个周日要花五,六个小时接送会友。她做最没有人愿意做的事:教儿童主日学,带小朋友。每个周末都忙着在家做饭、包饺子,请学生们来吃,给他们家的感觉,给他们爱,更给他们讲耶稣。用汗水和泪水,廿几年辛勤为主做工。或许她也不再时髦了,因为没有时间,也没有那些心思。她穿最简单的衣服,留最简单的短发。他们的代祷信里每次都附有全家的近照,每次我都感叹凌是那么朴素自然。很巧的是有次也同时收到大学同学的电邮,附了约廿个同学在华盛顿特区丽同学的漂亮大屋子里宴会的照片。丽当年与凌一起跳四人舞。同是大学里最出名的舞者,而且当时凌更加前卫,如今的生活是多么不同啊!当时我甚至不敢去问自己,如果让我选择,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凌吗?今天我才懂得,是神拣选了我们,拣选了凌和她的先生,而活在主引领的人生是何等的幸福。
她在走成圣的路,甘愿被主拆毁,让主重造。她信主后的经历,从最初的“在耶稣里得更丰盛的生命”到“我要服事神,我要得着能力,我要有荣神益人的见证”,再到这样的境界:“我们的舍己,通常是放弃世俗所追求的目标,然后是把我们的金钱、时间和才能奉献为主用。但我们内心还有一个最坚固的营垒,就是自我的喜好、向往,各种的情绪和所有的心思意念……”我还能说什么呢?只有深深的惭愧。直到今天,我只是刚刚能读懂她的心境,而实践,才在第一步:得更丰盛的生命,再加上服事神的心志。而那坚固的营垒,就是个人喜好和心思意念,从未想过连这些都要为主放弃。
感恩的是,神不曾放弃我。前不久看伍迪艾伦的《午夜巴黎》。这是一部我一直非常想看的电影。伍迪艾伦用他一贯的迥异于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很文化很艺术的手法,再一次展现浪漫迷人的欧洲。而且这一次做得最好,票房最高。不仅欧洲,连美国人也青睐。所以,夏天在洛杉矶,等我兴致勃勃跑到电影院,票已经卖完了。回到温哥华,电影已经下院,心情可以理解。最后只有坐在家里看的选择了。我倒了一杯红酒,准备享受一场盛宴。依然是伍迪艾伦,用迷人的镜头开场。更何况这次是巴黎,他用了近十分钟拍下最美的巴黎,特别是午夜。接下来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文艺青年来到巴黎。时光倒流,他午夜在酒吧里见到了海明威,一起喝酒聊文学。
“啊,生活就应该是这样!”我喝了一口酒,兴奋地对一旁的先生说。他不以为然。后来文艺青年又见到了其他历史上最著名的作家、画家,还跟他们一起生活,一同浪漫迷人。奇怪的是,一路看下去,我的兴奋感没有增加,甚至也没有持续太久。如果说几年前看伍迪艾伦的《午夜巴塞罗那》时我非常激动,还写了电影随笔;今天对《午夜巴黎》的评论是“也不过如此”,甚至感到它有点矫揉造作,也取消了写它的念头。不是电影不优秀,而是我的心态变了。生活不一定就应该是那样,神安放在我心里的,应该是更高的生活。
凌写那篇见证时,几乎是十年前了。今天的她,一定有更多美好的见证,我很想知道。她告诉我,现在很忙,一个人几乎要做四个人的工作,因为宣教同工里一个回去香港,另一人刚退休,求神为他们预备人;等空闲一点再跟我谈心。
在想着凌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的同时,自然就想到了教会的伟川师母:中央美术学院的高材生,著名青年美术评论家。廿年前的她用今天的标准也相当入时:白底黑条尖领的中长衬衫,白色的耳环,还有两条松散又很艺术的辫子。美丽,也同样时髦雕凿。我定睛在这照片上,她的神情不一样。今天的师母,她的眼睛和脸上有一种光芒,一种无比的喜乐和来自神的光。她又如何能不喜乐呢?她做着最快乐的事:为主做工;神也满足了她最大的心愿──先生成为牧师,还赐给她常人不可能得到的喜事:在42岁的高龄得到宝贝儿子。她也是留简单的短发,穿简单的衣服,美丽地走着成圣的路。
往事如烟,在基督里成为圣洁却是永恒。